《删除》从头再来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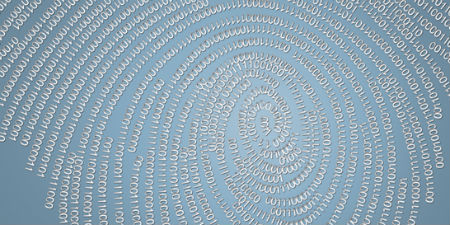
技术批评主义者对新技术批评中最喜欢使用的一招是:新技术违反人类天性(习惯)。电话刚出现不久的时候,英国人认为通过电话交流有违人们交往的“正常范式”,因为亲自去别人家拜访是当时人们更自然、也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交流方式;在电子书与纸质书的争论中,反对电子书的人很大的一部分理由也是读电子书让人“不习惯”或“不自然”。在文字刚出现的时候,苏格拉底则走得更远,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曾大力批判文字——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之一——在苏格拉底看来,文字不仅容易让人记忆力变差,还让人丧失口头表达的能力。两千多年后,许多人批评Google的论调也是这个理由:Google让人记忆变差。
与其他批评者不同的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先生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以下简称《删除》)一书中对信息数字化能长久无损保存记忆持一定的肯定态度,他所批评的是:记忆无处不在的年代,遗忘开始变得不可能。公共信息需要被长久记忆,但对于个人信息来说,我们需要遗忘。
舍恩伯格举了几个案例,说明遗忘(或“删除”)的重要性:一位想做教师的二十五岁单身母亲因为她在MySpace上发布的一张头戴海盗帽,举着塑料杯喝酒的照片,在校方发现后,被认为此举不适合当老师,被学校拒绝,失去了当老师的机会;另一位六十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因为他四十年前曾服用过致幻剂的内容上了网,被美国边境卫兵发现后,失去再次进入美国境内的机会。单身母亲和心理咨询师都想删除自己在网络上的记录,可惜Google早已索引。他们可以删掉源头,却阻止不了自己的信息在网络上被永久记录。
这其实引发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那些生于数字时代(born in digital)的人,比如90后、00后们,很多人从小就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发在网上,等他们长大成年进入工作时,他们是否会害怕未来的主管或公司看到自己青春期时的一些作为而感到苦恼和担忧?
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有点庆幸自己真正上网发生在20岁以后,而20岁以前的经历,尤其是那些迄今都不愿意在早年的同学中提起的经历,比如曾经的酒后失态,比如在报考大学时我特意选择了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的地方——就是为了重新开始,重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如果在YouTube/优酷和Facebook/人人网/新浪微博的年代,恐怕无论我跑到哪里,都很难与之前的联络人切断。即使切断联络人,Google和百度上也记录着你的经历,让我无处可逃。无法删除,意味着我失去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每个人都该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让这种可能变得尤为困难。
信息隐私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对自己的信息保留一定的控制,可以给一个人留有一些他需要的空间来定义他自己。除了失去第二次开始人生的机会,数字世界对个人信息的长久记忆也将导致数字原住民们想再塑造自己的身份变得更困难。人们在网上能看到你的过去,多年以后,其中有些你并不想让别人看到,或者时过境迁,你对事物的看法已经有所变化时,别人仍然认为你持有相反的看法,这将导致别人对你个人认知的混乱。说白了,当今的数字社会,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信息是否公布,但公布之后怎么传播、传播范围几何、以及传播之后是否可以收回,则由不得你。目前而言,我们并没有个人信息的完整控制权。,个人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舍恩伯格认为信息全面数字化之后,产生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所有的信息都去语境化了。在微博客和社交网站上,大多数信息都没有语境,没有背景,人们会因为其中某一句或激烈或极端的言论而引发转发或评论的欲望。如果这句话出现在一篇长文章中或一本书中,人们更容易接受,因为那句话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合适。单拎出来之后,往往刺激眼球。人们在脱离原有语境的情况下去理解单一信息,自然会产生偏差,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不过在《删除》一书的后半部分,舍恩伯格开始为批评而批评,很多论点站不住脚。遗忘是人类的天性——舍恩伯格仍以人的天性为着力点批评数字时代的缺陷。但我往往不屑于人的“天性说”,理由很简单:人的许多天性都不如机器好使,人天生不如汽车能跑,人天生不如挖掘机能挖土,但人类发明了各种机器,来帮助人们延伸自己的感官,去跑得更快、挖得更深、让声音传播得更远。
因为人类大脑记忆事物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这意味着你回忆的次数越多,年代越久远,你记忆中的事实与事物原本的真实度偏离得也越远。舍恩伯格认为,人们带着已经重构过的记忆再去看几十年前毫无偏差的事实时,会导致人们只相信数字化的信息,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可是,这不正说明人类大脑不擅长记忆事实性事物吗?对于人类不擅长的领域,且有技术能改进人类的缺陷时,为何仍要固守所谓人类天性呢?不如把事实性记忆交给机器,而把极为有限的脑细胞放在我们对往事的感受记忆和情绪记忆上,更加有针对性,更有意义,也更能解放我们的大脑。